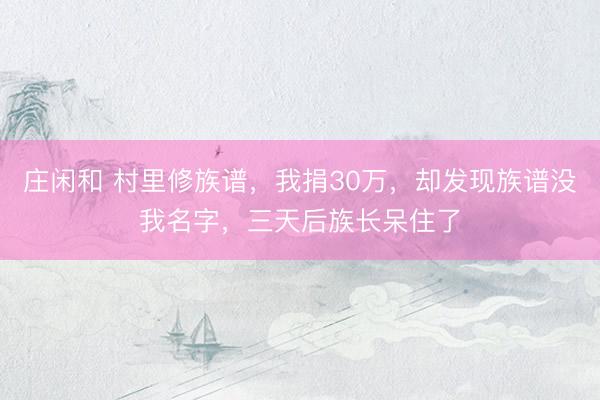
族谱摊开在祠堂的八仙桌上,密密匝匝的名字像一棵倒挂的大树,从明朝洪武年间的老祖先一直蔓延到当今。
我的手指顺着"德"字辈往下找,找了三遍,莫得我父亲周德才的名字。又顺着"建"字辈找,也莫得我周开国的名字。
咱们这一支,像是从来莫得存在过同样,被整皆地抹掉了。
三十万啊。我刚刚亲手把三十万的支票交到族长周德贵手里,墨迹还没干透。而当今,我站在这本簇新的族谱眼前,嗅觉我方像个见笑。
"开国啊,"族长的声息从死后传来,带着一种让我老成的、无出其右的腔调,"你也别往心里去。你爹当年的事,你是知说念的。族规即是族规,不可因为你当今有钱了,就把轨则改了。"
{jz:field.toptypename/}我转过身,看着这个头发斑白的老东说念主。他是我父亲的堂兄,本年七十二岁,在村里才高意广。此刻他脸上挂着一点似笑非笑的情愫,那情愫我太老成了——从我记事起,村里东说念主看咱们一家即是这种情愫。
"德贵叔,"我的声息很庄重,"我爹当年到底犯了什么事,要被逐出族谱?"
族长叹了语气,一副"你怎样还不解白"的形态。
伸开剩余92%"当年修祠堂的时候,族里凑了一笔钱,你爹精良守护。恶果钱丢了,整整两千块。那但是八五年啊,两千块是什么观念?够盖三间大瓦房了。"
"我爹说他没拿。"
"他虽然说没拿。"族长冷笑一声,"可钱是在他手里丢的,这是事实。族里开会表决,把他革职了,这亦然事实。开国,我知说念你当今前途了,在城里开大公司,有的是钱。但族谱是老祖先传下来的轨则,不可因为钱就坏了轨则。"
我看着他,莫得谈话。
三十万。这笔钱对于当今的我来说不算什么,但对于这个小山村来说,是一笔天文数字。通盘这个词修族谱的工程,预算也不外二十万。我多捐的那十万,本来是念念用来修缮祠堂的。
可当今,我的名字不在族谱上,我父亲的名字也不在。咱们一家三代东说念主,像是周家的一个罪过,被透顶抹去了。
"德贵叔,"我说,"这三十万,我不要记忆。但是我有一个肯求。"
族长的眼睛闪了闪,带着一点警惕:"什么肯求?"
"给我三天时分。三天之后,我会给您一个打法。"
族长看着我,似乎念念从我脸上看出什么头绪。但我的情愫很庄重,庄重得像一潭死水。
"行,"他终末说,"三天就三天。不外我把话说在前头,无论你查出什么,族谱的事,如故得族里东说念主开会表决。"
我点点头,回身走出了祠堂。
死后传来其他族东说念主的窃窃私议,但我莫得回头。
从祠堂出来,我莫得回城里,而是去了村东头的老屋子。
那是我设立的场所,一座破旧的土坯房,当今照旧莫得东说念主住了。父亲牺牲后,母亲随着我搬到了城里。但每年辉煌,我都会记忆给父亲上坟。
屋子比我回顾中更破了。屋顶的瓦片碎了几块,墙角长满了青苔。我推开那扇咯吱作响的木门,一股霉味扑面而来。
我站在堂屋中间,环视四周。墙上还挂着父亲年青时候的像片,像片照旧发黄了,但父亲的笑貌依然澄澈。当时候他才三十露面,眉清目秀,意气昌盛。
八五年的事,我其实不太铭刻。那年我才五岁,只铭刻有一天,家里顿然来了许多东说念主,吵喧噪嚷的。母亲抱着我躲在里屋,我透过门缝看到父亲跪在堂屋中间,额头上全是血。
其后我才知说念,那天是族里开会,说父亲偷了修祠堂的钱,要把他逐出族谱。父亲不屈,和东说念主争握起来,被东说念主禁绝了头。
从那以后,咱们一家就成了村里的"贼"。走到那里都有东说念主指带领点,小孩子见了我都绕着走。上学的时候,同学们骂我是"贼娃子",我和东说念主打架,憨厚不分青红皂白就罚我站。
父亲在村里抬不入手,只好出去打工。但他身段不好,在工地上干了几年,落下寂寞病。我十五岁那年,他走了。临终前,他拉着我的手说:"开国,爹莫得偷阿谁钱。爹这辈子明昭着白,没作念过负隐衷。你要深信爹。"
我信他。从始至终,我都信他。
但"信"是一趟事,"证明"是另一趟事。三十九年了,当年的事情还能查澄澈吗?
我在老屋子里待了很久,倾肠倒笼地找了一遍。在父亲的遗物里,我找到了一个发黄的条记本。那是父亲的账本,上头记取当年修祠堂的每一笔进出。笔迹工奥密整,每一分钱都有出处。
账本的终末一页,写着一排字:"钱交给德福守护,收条附后。"
德福?周德福是谁?
我皱起眉头,艰苦回忆着。周德福......是族长周德贵的亲弟弟,当年是村里的管帐。但他好像很早就牺牲了,我铭刻过问过他的葬礼。
收条呢?我把通盘这个词条记本翻了一遍,莫得找到任何收条。
但这至少证据一件事:当年那笔钱,父亲也曾交给了周德福。
我决定去找周德福的家属问问。
周德福的女儿叫周建军,比我大几岁,当今在镇上开了一家五金店。我开车去了镇上,找到了那家店。
"开国?"周建军看到我,有些惟恐,"你怎样来了?"
"建军哥,我念念问你点事。"我开门见山,"对于八五年修祠堂的钱,你知说念几许?"
周建军的神采变了一下。他把我拉进里间,关上门,压柔声息说:"你问这个干什么?"
"你应该知说念,我爹被逐出族谱,即是因为这件事。"我看着他的眼睛,"我念念知说念真相。"
周建军千里默了很久。我看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。
"开国,"他终于启齿了,"有些事......我亦然其后才知说念的。"
"什么事?"
他深吸衔接,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。
"我爹牺牲之前,跟我说过一些话。他说......他这辈子作念过一件负隐衷,抱歉你们一家。"
我的心跳加快了。"什么负隐衷?"
"八五年那笔钱,照实是你爹交给我爹守护的。但我爹......我爹把钱给弄丢了。当时候他赌博,把钱输掉了。"
我呆住了。
"其后族里追查这笔钱,我爹发怵,就......就把职责推到了你爹身上。他把收条藏了起来,说钱一直在你爹手里。"
我嗅觉血液在往头上涌。三十九年了,我父亲包袱了三十九年的骂名,蓝本是被东说念主败坏的。
"建军哥,"我的声息有些发抖,"那张收条呢?"
周建军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子,掀开,内部是一叠发黄的纸。他翻了翻,找出一张。
"这个......我爹牺牲后,我在他遗物里找到的。本来念念烧掉,但下不了手。这些年一直锁在这里。"
我接过那张纸。那是一张手写的收条,上头写着:"今收到周德才交来修祠堂款项贰仟元整,经手东说念主周德福。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。"
笔迹大肆,庄闲和游戏app但清澄澈楚。
我的眼眶热了。父亲,蓝本你确实莫得骗我。
"建军哥,"我把收条收好,"谢谢你。"
周建军的眼睛也红了。"开国,抱歉。咱们家......欠你们家的。"
我摇摇头。"这是你爹作念的事,不怪你。"
我回身要走,周建军顿然叫住我:"开国,你......你要怎样作念?"
我停驻脚步,莫得回头。"该怎样作念,就怎样作念。"
回到村里,我莫得坐窝去找族长。我先去了镇上的公证处,把那张收条作念了公证。然后,我又找到了几个当年参与过修祠堂的老东说念主,录了他们的供词。
三十九年前的事,许多细节他们照旧记不清了。但有一件事他们都铭刻:周德福当年照实有赌博的习气,并且在那笔钱丢失之后,他顿然就"戒"了。
第三六合午,我召集了通盘的族东说念主,在祠堂开会。
族长周德贵坐在正中央,神采有些丢丑。他约略照旧传说了一些风声,但他不知说念我手里到底有什么凭据。
"开国,"他动身点启齿,"你说要给公共一个打法,当今不错说了。"
我点点头,站起身来,环视四周。祠堂里坐满了东说念主,黑压压的一派。有些是我意识的父老,有些是和我同辈的兄弟,还有一些年青的小辈,他们酷好地看着我,不知说念今天会发生什么。
"诸位叔伯、兄弟,"我说,"今天把公共叫来,是为了八五年那件事。"
东说念主群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议。
"我知说念,这些年在村里,咱们一家名声不好。我爹被说成是贼,我从小被东说念主骂'贼娃子'。三十九年了,咱们一家一直背着这个骂名。"
族长咳嗽了一声:"开国,以前的事就让它以前吧。你当今前途了,何须......"
"德贵叔,"我打断他,"请让我说完。"
我从包里拿出那张收条,递给掌握的东说念主传阅。
"这是当年的收条,是我爹把钱交给周德福叔时,周德福叔亲笔写的。这张收条证明,那两千块钱,我爹早就交出去了。"
祠堂里一霎安闲了。
我又拿出一份公文凭。"这是镇上公证处的公证,证明这张收条的信得过性。另外,我还找到了几位当年的知情东说念主,他们不错作证,周德福叔当年有赌博的习气。"
东说念主群开动弘大了。有东说念主在小声谈论,有东说念主把眼神投向族长。
族长的神采变得很丢丑。他念念说什么,但嘴唇动了动,莫得发出声息。
"德贵叔,"我走到他眼前,"我知说念周德福叔是您亲弟弟。他照旧牺牲了,我不念念根究他的职责。但我父亲清白了一辈子,他不可带着贼的骂名入土。"
族长低下头,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我回身面向通盘东说念主:"今天我来,不是为了翻旧账,不是为了舛误谁。我只消一个肯求:把我父亲的名字,再行写进族谱。他是周家的子孙,他莫得作念抱歉族里的事。"
祠堂里千里默了很久。
终于,一个年迈的声息响起来。是村里最年长的周德祥老爷子,本年九十三岁了。
"德贵,"他晃晃悠悠地说,"开国说得对。德才当年是被冤枉的,这个错,咱们得认。"
又有几个老东说念主推奖:"是啊,该改就改,不可让好东说念主蒙冤。"
族长的嘴唇在发抖。他迟缓站起身来,看着我,眼睛里有傀怍,有无奈,还有一点我看不懂的情谊。
"开国,"他的声息很轻,"抱歉。"
我呆住了。我没念念到他会说念歉。
"当年的事......我其实是知说念的。"他说,"我知说念是我弟弟拿了那笔钱,但他跪着求我,说如若被发现了,他就没脸活了。我......我就帮他瞒了下来。"
祠堂里一派哗然。
"这些年,我一直过不去心里那说念坎。每次看到你们一家耐劳,我心里都不好受。但我......我不敢说。说了,我弟弟的名声就完毕,咱们这一支就完毕。"
他"扑通"一声跪在了地上。
"开国,我抱歉你爹,抱歉你们一家。你要打要骂,我都认。"
我看着这个七十二岁的老东说念主跪在我眼前,心里说不出是什么味说念。恨吗?三十九年的冤屈,怎样可能不恨。但看着他满头的白首和期凌的眼泪,那股恨意又迟缓淡了下去。
"德贵叔,"我弯腰扶起他,"起来吧。我爹临终前跟我说过,让我不要记仇。他说,冤冤相报何时了,清者自清就好。"
族长呆住了,满面泪痕。
"我父亲是个敦厚东说念主,他一辈子最敬重的即是眷属和乡亲。他如若知说念今天闹成这么,笃定不欢笑。"我顿了顿,"是以,我不根究了。只消把他的名字写进族谱,让他阴曹阴曹能镇静,就够了。"
那天晚上,族里开了一个纯粹的庆典。在通盘东说念主的见证下,父亲的名字被再行写进了族谱。周德才,开国的父亲,周家的子孙,明昭着白的一个东说念主。
我站在祠堂里,看着族谱上那三个字,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爹,你看到了吗?你女儿给你正名了。
庆典截止后,我在村里住了一晚。第二天一早,我去给父亲上了坟。
坟前的草照旧很高了,我蹲下身,一根一根地拔掉。
"爹,"我说,"事情办完毕。你的名字回到族谱上了。"
风吹过山坡,带来一阵松涛声。我朦胧合计,那是父亲在薪金我。
"爹,你释怀吧。我会把日子过好的。"
我在坟前坐了很久,直到太阳升高,才站起身来。
临走前,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土坯房。屋子很破旧,但它是我的根。无论我走多远,这里耐久是我的家。
回城的路上,我接到了周建军的电话。
"开国,谢谢你......莫得根究。"
我笑了笑:"都是一家东说念主,说什么根究不根究的。"
"以后......以后有什么需要帮衬的,你说一声。"
"好。"
挂了电话,我看着窗外速即倒退的风光,心里独特别庄重。
三十万,买回了父亲的清白,买回了我在族谱上的位置。值不值?我合计值。不是因为阿谁名字有多伏击,而是因为,有些事情,总要有一个了结。
我念念起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:"作念东说念主要明昭着白,言之成理。"
他作念到了,我也会作念到。
故事讲到这里,差未几就截止了。但我念念问问公共:如果是你,你会聘请原宥吗?
有东说念主可能会说,三十九年的冤屈,怎样能说原宥就原宥?有东说念主可能会说,冤冤相报何时了,放下技术上前走。
我不知说念什么才是正确的谜底。但我知说念,当我扶起族长的那一刻,我嗅觉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也许,这即是所谓的"释怀"吧。
发布于:河南省